|

李广田〔1906.10.1-1968.11.2〕,中国现代诗人,且是著名散文作家。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,1968年11月死于昆明。他出生在一户王姓农民家里,排行第四,取名锡爵。由于家境贫寒,出生不久便被“借给”中年无子的舅父,改姓李,名广田。幼年曾读过私塾。他的童年是在孤独与贫困中度过的。
1923年入济南第一师范后,开始接触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思想、新文学。
1926年入团。他和朋友们组织书报社,大量介绍文研会、创造社,未名社及苏俄作品。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预科,在《未名》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散文《狱前》。文章以内心独白的议论手法回顾自己的狱中生活,表达了他为真理视死如归的胸怀。其间先后在《华北日报》副刊和《现代》杂志上发表诗歌、散文,并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。后出版三人诗合集《汉园集》,被人称为“汉园三诗人”。
1935年北大毕业后回到济南教书,其间完成了许多散文,出版了《画廊集》《银狐集》《雀蓑记》等。内容多为故乡童年的回忆和抒发对现实不满的情绪。抗战爆发后,流亡南下,辗转于河南、湖北、四川等地。这时期完成了《圈外》散文集。1941年到昆明,在西南联大任教。这时期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引力》,这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,表现出反战抗日的主题思想,在国内外引起一定反响。其间还出版了散文集《灌木集》《回声》《日边随笔》;短篇小说《欢喜团》《金坛子》和论文集《诗的艺术》。抗战胜利后,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,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。1948年加入共产党。
1949年在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文联委员、文协理事。1952年调任云南大
学副校长、校长。历任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,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,中国作协理事等。文革期间他遭受四人帮摧残致死。
李广田是中国现代文坛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。冯至先生称:“广田的散文在乡土文学中是独树一枝的。”他的散文朴实、淳厚,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繁星读书网 2009.03.14
|
---- 相关资料 ----
 暂无
暂无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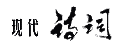 |
|